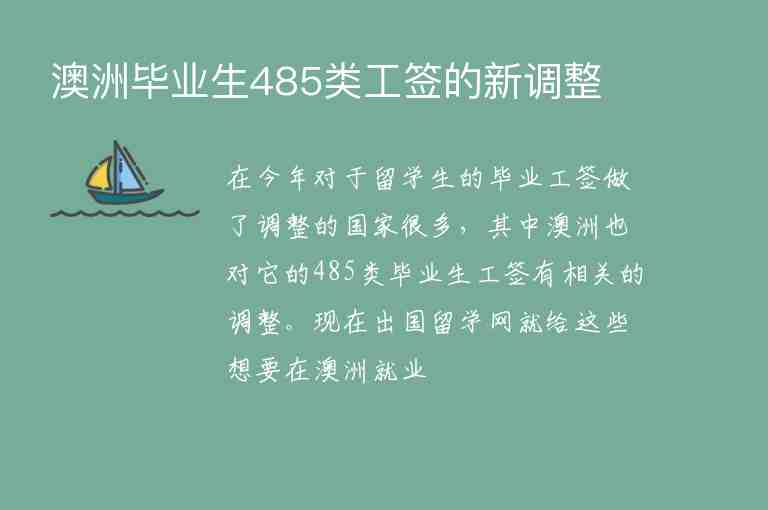布兰迪斯大学副教授王璞
《本雅明传》,【美】霍华德·艾伦、迈克尔·詹宁斯着,王璞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908页,145.00元
“矛盾而流动的整体”
“……我的不同信仰所代表的矛盾而流动的整体”—— 二十世纪犹太裔德国批评家、理论家和文学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曾这样描述他的思想生活。他多样的作品、不幸的经历和迟来的名声在英语和汉语世界仍然散发着近乎神秘的吸引力。 2014年夏天,当我第一次收到翻译《沃尔特·本杰明:《批判的人生》的邀请时,我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本传记是“第一本完整的英文传记”,出自霍华德·艾兰和迈克尔·W·詹宁斯的《四只手》。当我上大学时,在图书馆浏览沃尔特·本雅明著作的英文译本时,我就已经注意到这两位本雅明专家的名字。艾伦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长期文学讲师。詹宁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德语教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编辑林赛·沃特斯的大力推动下,哈佛大学出版社成为本雅明作品英译的重要中心。这两位学者的努力与合作贯穿了哈佛出版社的各个版本。汇编四卷《瓦尔特·本雅明文选》(沃尔特·本杰明: 著作选集)。 1996年至2003年,这部选集终于出版,至今仍是英语世界本雅明作品较为完整的呈现。同时,艾兰也是本雅明遗稿《拱廊街计划》(《拱廊计划》)和专题选集《现代生活的作家——论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作家》: 波德莱尔随笔)的英文翻译者之一。詹宁斯不仅编辑了《现代生活的作家》,而且还是《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及其他讨论媒介的文字》(技术再现时代的艺术作品和其他媒体著作)的编辑之一。这些译本也在本世纪头十年被哈佛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可以说,2014年哈佛出版社版《本雅明传》是这个全面介绍本雅明遗产的长期项目的收官之作,甚至感觉像是一个高潮。
《瓦尔特·本雅明文选》 (1996-2003)
《现代生活的作家——论波德莱尔》 (2006)
《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及其他讨论媒介的文字》 (2008)
说起我自己,高中时第一次看到《高级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胜译)这个书名时,我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但尽管我和其他文艺青年、文科生一样,早已将本雅明的形象印在了脑海里,但每次翻开这本不厚的译文,我只能在震惊和眩晕中来回跌倒,陷入历史的空白。意象的边界纪念碑之间(但文化批评如《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似乎更容易进入)。真正读完《发》后,我已经是一名硕士生了(我最早的评论之一也是以此为标题的)。在北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我沉浸在本雅明选集《启迪》(张旭东、王斑译,当时只有香港牛津版)中。抬头一看,秋光慢慢地透过金黄的银杏叶洒下来。 —— 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自己有幸成为本雅明中文翻译家张旭东先生的学生。在纽约大学读书期间,我和同学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共同翻译了《拱廊街计划》。 2008年秋冬,我去巴黎游学。穿过拱廊,进入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老图书馆。本雅明曾在这里“隐藏”(用他自己的词geborgen)来深刻描述十九世纪的商品资本。《拱》的引文被收集成浩瀚的宇宙,辩证的图像如星团般闪烁。 ——,作为一名从中国经“新世界”到“旧欧洲”的学生,我确实感觉到主阅览室拱顶上刻着的各大城市的名字仍然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我一边翻着本雅明引用的法文资料,一边通过张老师修订的新版《发》重新调整自己在德国犹太人本雅明和“资产阶级世纪”之间的立场。于是我决定将Benjamin的著作纳入我的博士考试题目,并请Richard Sieburth教授(《莫斯科日记》的英文译者)给予我这方面的指导。 2012年毕业后,我去布兰迪斯大学任教。这所美国大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犹太精神传统。甚至可以说,作为美国最年轻的研究型大学,它的成立也是对犹太人所经历的现代苦难的回应。这也让我想起了本杰明在逃往美国途中的死亡。此刻,我有机会向华人世界介绍《本雅明注释》的英译本。我自然很兴奋。在拿到样书之前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我什至觉得我真的注定要成为本杰明遗产的一部分。
然而,这个“命运”很快就展现出了一种“魔力”的力量。正如本雅明的一生似乎无法逃脱“厄运”和“危险”一样,这部传记的翻译也一再拖延,伴随着“小我”和“大我”的跌宕起伏。不仅因为我个人学术晋升过程中的焦虑和痛苦而一再拖延,而且,在生命的崩溃中,它也见证了我们所生活的历史场景的构造运动。 2019年,我终于完成了翻译草稿。我在法国游学期间想修改一下,但没想到,全球COVID-19疫情来袭。当我恢复翻译工作时,我已经经历了法国、美国、中国的防疫考验。这次拖延,大概是因为我计划上的“笨拙”,以及我对“驼背小个子”独特的“亲和力”。在时代风气的变迁中,翻译几乎成了一出“丧剧”。 —— 我们他的处境可能比本杰明幸运得多,但也到处都有灾难的迹象。我什至不禁想起本杰明创办出版物的多次失败,出版计划的多次停滞,死胡同和逃亡。我几乎感觉命运即将降临:这个翻译难道终于无法完成了吗?学校改革之际,我得知艾伦已经从麻省理工学院退休,林赛·沃特斯也不再担任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主编。疫情期间,林赛每次给我打电话,我都不好意思汇报进展情况。相反,资深编辑安慰我说,把这么大的传记翻译成中文,费时又费力。确实,当我需要为近八年的拖延找借口时,我总是首先提到的就是这本书的厚度。厚度或许是这本书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它太厚了,根本无法拿在手里阅读(英文原版近800页,德文和西班牙文译本均超过1000页)。当翻译完成后,我想强调这一基本特征也与这本传记的意义有关。我想称之为“批判传记的可能性”。
《本雅明传》 英文版封面
正如比较文学学者大卫·费里斯在他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该书的沉重“分量”正是传记的意义。在他看来,艾伦和詹宁斯是本书作者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对本雅明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着传记写作的特殊“任务”。在二十世纪思想史和批评史的种种困境中,本雅明的传记如何可能?本书的厚度源于传记的丰富。它不仅是英语世界,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内容最丰富、最完整、最全面的本雅明传记。这就是为什么当它被翻译成德语(本杰明的母语)时,甚至登上了德国(本杰明的祖国)非小说类图书的畅销榜。德文译本由Suhrkamp出版,出版号《本雅明全集》。德国书界将这本书宣传为“细节”筑成的“丰碑”。
当然,在此之前,我们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一系列本雅明的思想肖像:具有通灵气质的左翼同路人、艺术中的救世主、资本主义普遍危机中的飞翔天使、语言障碍世界中的水下采珠人。和欧洲犹太传统。异类,物质世界的流浪者,资产阶级梦想的收集者和追忆者,精神气息消失后的文体实验者,密宗式的政治神学家,边缘史料中的拾荒者,法兰克福的编外人员学校、经验世界的哀悼者和技术团体的倡导者等等。两位传记作者还在本书《尾声》 中指出,在本雅明的死后名字中,“他的人生故事笼罩在神话之中……当解释者捕捉到他思想的各个独特方面时,存在无数的差异。”本雅明也开始出现。”以往的评论者习惯于从某个主题出发,对本雅明的思想历程进行叙述。这些叙述虽然有时相互矛盾,但都是自证其说的,因为不难从中找出端倪。关于本雅明的现有文献:“沃尔特·本雅明的生活和作品为所有这些构建提供了材料。”
过去对作家的研究,无论是传记性的还是批评性的,都倾向于选择性地处理问题,对本雅明的作品强加一定的主题顺序,这往往会消解他作品的整体方面。结果往往是一幅局部的、或者最坏的情况下甚至是神话化的、扭曲的肖像。这本传记追求一种更全面的方法:它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展开,关注本雅明写作出现的日常现实,并为其主要作品提供思想历史背景。这种定位使我们能够关注他人生各个阶段的历史性,从而关注他各种作品的历史性。它们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时刻和本雅明自己的意识形态关注。我们也必须充分相信这种显而易见、可感知的思想发展轨迹。
因此,这本传记并没有提出、更不用说强化本雅明的任何一维观点。如果非要给这本书加上一条“主线”,就必须回到作者反复引用的本雅明自己的话:“我一直按照自己的信仰来写作……但我从来没有试图表达我的多元化”。信念所代表的矛盾且流动的整体。”在本雅明一生的历史“赌博”中,我们看不到“真相牌”,那么“整体”的“可信度”从何而来?包括所谓的“小”作品和大量信件,还包括他们孜孜不倦地收集与本杰明有关的所有细节,正如费里斯的书评所说,这些细节几乎包罗万象,“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智力的,特别是,我们需要记住,本雅明的大部分相关材料都已丢失。有些是在德国、美国和以色列收集的,有些则留在了苏联和东德档案馆的秘密角落里。法国国家图书馆丢失的这些零散信息也是本雅明一生的征兆,两位作者通过近乎详尽的搜寻,编织出了一个“矛盾而流动的整体”,使这本传记成为一部全面的信息集。以及本杰明研究的“基准著作”。这本书的编辑Lindsay Shui也向我表示,在他心目中,这是传记不可替代的价值之一。
详细“纺织”和评论的可能性
然而,在大量的细节中,作为一名译者,我也产生了疑问。我真的需要知道这么多吗?我真的需要知道本杰明小孩子的第一个性幻想来自于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妓女吗?这本书对一位重要女性——本杰明的妻子多拉·波拉克(Dora Pollak)的描绘令我感动。她对本杰明才华的极度钦佩和离婚后对前夫的大力支持读起来令人沮丧。但我必须读她最私人的信件吗?多拉曾形容她的丈夫“没有身体”,在离婚诉讼期间,她相信本杰明在与拉脱维亚苏联人阿斯雅·拉西斯在一起时,脑子里“只有性”(传记作者总结道,本杰明“除了性什么都没有”)在他的脑海里)。在本雅明的“脱离实体的光环”下流淌着“暴力的肉欲能量”和“性冒险主义”)……本雅明和玛格丽特·卡普鲁斯(Margarete Karpurus),也就是后来成为阿多诺的妻子“格蕾特”·卡普拉斯(Gretel Karplus)的关系,我们是不是要验证一下关系到底有多亲密?我必须喜欢他和格肖姆·肖勒姆秘密编撰的那些大学笑话吗?我们是否需要知道同时代的德国学者在争夺研究经费和职位时是多么的精打细算?这些细节对于理解本雅明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他的思想的辩证节奏有多大帮助?费里斯在书评中认为,这本传记并没有提出对本雅明的颠覆性观点,而只是“安静地、平静地、有说服力地”构建了一个“仔细而精确的综合”。这也代表了英语学术界对本书的总体评价。传记的丰富来自于细节的丰富,而细节又融入了叙述的平实。德译本的审稿人甚至专门引用了本雅明在《音乐》、《建筑》和《纺织》中的文章《三步走》来衡量这部传记。可以说,平淡是传记的基调,厚重是传记的建筑感,丰富是传记的编织手法。
肖勒姆(1925)
我曾担心,传记散文的细致编织,虽然抗拒单一的主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会压倒本雅明的辩证机智、“深思熟虑的图像”的闪现和哲学思考的光彩。色彩之间的色调、他的概念和情感。这种漫长的流动,就像一部缓慢的悲剧剧,最终不同于本雅明著作中“感官体验”和“智力体验”的互动(我的导师希布斯教授似乎有这样的保留,不喜欢这本书太长)。一位评论家表示,这本传记告诉了我们“很多”信息(比如他对某些“纸质文具”的挑剔和偏爱、他对海岛旅行的热情、他的“赌瘾和吸毒”),但给人的感觉“生活细节优先于思想成果及其内涵”。一些评论家的态度更为严厉,认为该书擅长“无关紧要的细节”,传记的叙述偏向于本雅明的日常经历,具有“自闭症”的特征,未能将“微小的细节”结合起来。生活与政治。历史的“大势”与思想上的“大论”有效衔接。这种批评确实不公平,但我们确实需要思考:细节如何“编织”本雅明一生作品的“整体”,传记的“任务”如何可能?
也是随着翻译时间的不断延长,我开始体会到细节逐渐释放的能量。我逐渐接近了本雅明作品中的片段、碎片和小插曲。这些“小”著作并不是批判理论的“名著”。有时,它们在英文或中文译本中都找不到,但它们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传记纹理。在传记中,它们徘徊在日常生活中,把我作为细节和部分带入生活世界,而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具体轮廓中,本雅明的思想作品才作为经验出现。例如,这本传记将1929 年视为本雅明生活中各种元素汇聚的关键点。今年的叙事特别多调,这些调之间的过渡细节深深吸引了我。这不仅是本雅明离婚的一年,也是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年。同年,他与布莱希特建立了友谊,并完成了对普鲁斯特的评论。而在离婚诉讼的“残酷性”显现出来之前,他不止一次出国旅行(他的一生都是“一个流浪的学生,不断寻找新的开始”)。所以这本传记让我们跟随本雅明来到意大利。访问圣吉米尼亚诺后,他写道:
要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眼前的事情是多么困难啊。当这句话最终出现时,他们用小锤子敲击真理,直到他们像从铜片上凿出图像一样。 “晚上,妇女们在城门前的喷泉边从大瓶子里打水。”直到我找到这些话,这个凹陷、阴影深重的形象才从一次过于眩晕的经历中浮现出来。上升。
圣吉米尼亚诺
他接着谈到亚平宁的太阳是一块闪亮的石头:“前几代人一定有一种技能,知道如何保存这块石头作为护身符,从而将时间变成恩典。”这些话被具体化为游记《单行道》(圣吉米尼亚诺),发表于《圣吉米尼亚诺》(法兰克福报)。它没有完整的英文翻译。当我看到传记中的摘录时,我感到全身颤抖。托斯卡纳风景的美丽和德语文字的优美是难以想象的(我蹩脚的翻译也无法抵消它们)。本杰明将这篇文章献给当时刚刚去世的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但他的忌日恰好是本杰明的生日。
两位传记作者概述了贯穿本雅明精神活动的三个主题:生活经历、历史记忆以及作为两者的绝对媒介的艺术。在这样的诗意素描中,我们看到了三者融合的极其微妙而又明显的可能性。生活经历在历史的阳光和时间的跳动下成为艺术。同样,本雅明的一生也被赋予了在这本传记中历史化的媒介和必要的时间。只有在尽可能多的细节的“小锤子”的打击下,本雅明的真实存在才能作为历史记忆的图像出现在“铜盘”上。正如本雅明笔下的每一个“字”一样,每一个细节也可以成为一个“矛盾而流动的整体”的中心,既发散又聚合。传记让细节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工作。
细节中的“时刻”既指本雅明的一生,也指两位作者在数十年的工作后面临“传记任务”的时刻。这甚至是属于译者和读者的时间。在多年的翻译过程中,传记中的一些细节被仔细收集和严格审查,而另一些细节则被两位作者捡到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本杰明一直在记录儿子的“意见和想法”,观察孩子的语言习得和颜色识别,而这些私密的话语也蕴藏着家庭生活的创伤。我不仅理解了本雅明的模仿理论与他作为父亲的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我什至开始研究我自己的孩子。是的,这本传记的翻译也恰逢我孩子的成长。在法国的那些春夜,我想起了本雅明对比利时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的痴迷。本雅明的许多关于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化的讨论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在翻译这本书之前,我并不了解这位推理小说大师一生的地位:1930年代的困难时期和“灰暗”的时期。 《时间》,西默农的法国小说是“最好的救援”,陪伴他度过了许多孤独的夜晚。在伊维萨岛,他与数百只苍蝇一起生活,并在烛光下阅读西默农的小说。我也可以尝试去见见“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本杰明吗?也正是在疫情期间的修改过程中,我又回到了第一次翻译时没有特别注意的一个“小节”:1918年,“西班牙流感”肆虐欧洲,本杰明和他的妻子被感染了,但症状很轻微,而此前不久,他们刚刚搬到瑞士伯尔尼,“搬进了一套四居室的公寓,并雇了一名住家女佣”。在他的人生后期,当本雅明修改并完成了《法兰克福报》的“最终草案”时,他在记忆问题上发展了疫苗接种的隐喻。他这样描述“疫苗接种的好处”:
那时在意大利,我已经开始明白,我即将要与我出生的城市进行长久甚至永久的告别。我在内心生活中多次体验到疫苗接种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继续遵循这种方法,并刻意地想起流亡期间最能引起怀旧的那些画面:童年的画面。我的假设是,就像疫苗无法主宰健康的身体一样,渴望的想法也无法主宰我的精神。我试图通过理解过去的不可逆转性并不是偶然的传记意义上的不可逆转,而是社会意义上的不可避免来抑制渴望的影响。
童年本杰明
这接近于“普鲁斯特+历史唯物主义”。在即将到来的战争阴影下,在日益漫长的流亡生活中,童年记忆是一种疫苗,用最能唤醒怀旧的意象来防止怀旧主宰精神。 1938年的这段话也隐含地提出了传记的可能性,这不是生命史的偶然,而是来自历史记忆的不可逆转。另一个相关的隐喻细节,将历史时间比作太阳的运动,也来自本雅明晚期的书信。他告诉肖勒姆,他的存在最终将在“太阳的历史进程中”被理解,他的作品将成为一种测量仪器,让“最慢”运动的最微小的段落转化为“历史索引”。精美的纺织品“慢慢”形成了细致的历史感。
最终需要衡量的是流放的时间,迷失的时间。顺着传记的时间顺序,我怀念的不仅是人的分散,还有物的转移。 —— 本杰明是一位收藏家。他的书籍、儿童画册、玩具和艺术品在欧洲“饱含泪水”。 “气氛”中发生了怎样的转运转售?他的手稿已沿着他逃亡失败的“三角路线”被“转移”到巴勒斯坦、苏联和美国,而留在柏林的部分将出现在盖世太保的档案中。他一生的收藏最终成为他翻山越岭前往法国与西班牙边境时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包”——。其中的“新手稿”到底是什么,是连传记都无法解开的“谜”。在时间“太阳”的运动中,在“进步”的劲风中,所有与本雅明有关的小文字、大大小小的物品都承载着一条“不可逆转”的通道,走向不可能的救赎或“万物的复兴”。 ” 空缺,向着博物学的死亡浪潮,向着我们。我对“矛盾而流动的整体”中的人、物、景、事件、关系产生共情,不仅是因为翻译产生的“代入感”,更多的是因为历史时间的“叠印”。翻译的处境、传记的叙述以及本雅明的生命过程都被“套印”起来,仿佛有一种微弱但却必要的“可识别性”,因为我们的存在也是历史通道的一部分。
我不能再忽视那些在翻译中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部分”。我什至无法忘记本杰明在巴黎贝纳德街公寓里的室友。她的名字叫乌塞尔·巴德,也是一位流亡的德国犹太人。然而,她与本杰明完全不同。她并非出身于上层资产阶级家庭,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是一名年轻的文员。他甚至因为转租问题与本杰明发生了小冲突。显然,她和本雅明之间并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交流和精神上的联系,但传记却从本雅明的生活细节出发,顺带转向了这样一个“普通”犹太年轻女子的命运。两位作者告知,布德在战争期间也被关押在法国战俘营中。 1942年,她试图逃离马赛。 “从那以后,她的所有踪迹都消失了。”背离、偏转和横向:我们仅仅得到“细节”吗?随着翻译的进行,我的心越来越依恋乌泽尔·布德等“小事”,因为这些也是本雅明思想、生活、工作、身心崩溃的特定历史情境的一部分。发生。我也越来越认识到,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线索并不是外在的,而是“矛盾的、流动的整体”的内在。细节所释放的潜力,正是这样一部批判传记的意义所在。由此看来,本雅明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包括了由各种拱廊、思想线索、生活路径所形成的秘密交集网络,分叉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秘密角落,而且还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单子,展示着历史。真理的复兴力量是神秘的、具体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细节的能量指向评论的可能性。原书的副标题是“A Critical Life”,直译过来就是“批判传记”。然而,考虑到英语中“批判”一词的多义性和德国思想中关键词“批判”的内涵,考虑到“批判”概念在本雅明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考虑到本雅明曾经立志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德语世界。 “批评”,我觉得这个副标题还有其他含义,或者可以引申翻译为:“批评/批判生活”、“批判生活”、“重要生活”……我的想法也得到了证实,艾伦在信件中得知,多重意义确实是作者的初衷(值得一提的是,詹宁斯的第一本学术专着就是基于本雅明的文学“批评”理论)。批判传记,即批评传记,需要呈现一个不断释放批判潜力的人生。换句话说,批判传记的真正对象应该是对生活的“批判”。而“批判性”正是本雅明的理念。 2008年秋天,我参加了塞缪尔·韦伯教授在巴黎举办的每周研讨会。当时,他关注的是本雅明的一系列“可能性”概念:可批评性、可传播性、可译性、可引用性、可复制性和易读性。在本雅明的理论中,作品的可批评性、可传播性和可翻译性都涉及到艺术的“晚年生活”。或许可以说,批评传记也是传记的“后来的生活”,而“整个”生活因此在后来的历史时间中变得可批评、可传达、可翻译、甚至可引用。这就是批评传记作为“评注”的可能性。两位作者尽力将每一个细节都呈现为线索和路径,分歧进入历史,同时将每一个细节都视为“整体”的潜在中心。他们特别指出,本雅明的写作总是在细节的“力场”中获得“整体感”。这部批判传记也获得了让丰富的细节在“后来”的时间里释放潜力、产生“生命”的可能性,为历史的阳光“照亮”本雅明的“整体”提供了条件,为进一步的“经验和记忆的测量”。在与我们自身历史存在的关联性中,我的翻译作为一种“晚年生活”,也成为批判传记可能性的一部分,成为本雅明一生的“可批判性”和“可译性”。部分。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