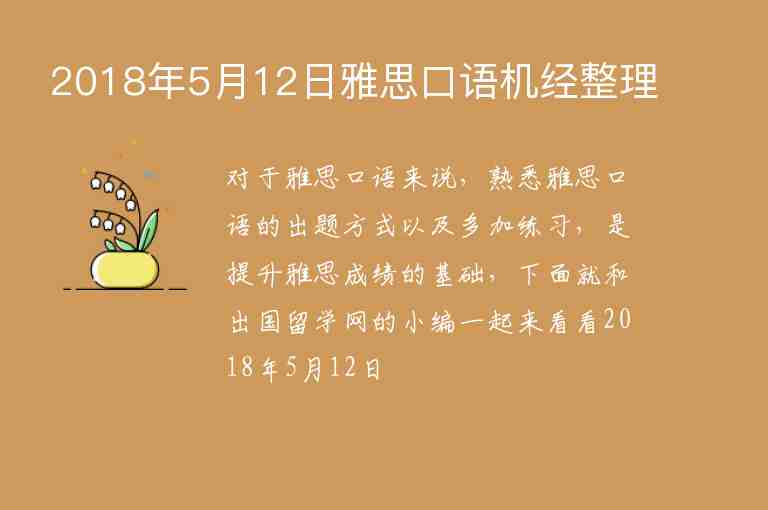导语:受疫情和暴雪天气影响,近一个月来,美国多地航空业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混乱:从大面积延误,到国际航班中途返航,估计很多人都再也回不来了。有想过在美国坐飞机。实际上可能就像一场噩梦。本文作者讲述了这样的经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家高田滚滚】
很多年后,当我回首往事,开始后悔在大洋彼岸浪费了时间时,我一定会想起最后一天按下购票确认按钮时那个愚蠢、鲁莽、不可逆转的下午。 2021 年.
这一切都要从半年前的盛夏——说起。因为我通过微信联系人发现,有一位老同学也到了美国。在异国他乡见到老朋友的兴奋中,我愚蠢地向朋友许诺“新年在某家夏威夷餐厅见”。 “承诺的——位朋友在美国的另一个角落(不是夏威夷)。
12月初,我有一次放弃的机会,但我没有抓住,订了机票。 1月初,Omicron变种病毒开始传播,我计划中的第一张机票被取消了。这时候,我又有了一个既省钱又不得罪人的机会。不幸的是,我越穷越笨,我就越想挽回面子。再说了,我小心翼翼这么久了,已经坚持不住了。我并不珍惜这次机会,我选择了放弃。
所以我亲眼目睹了美国民航现在有多糟糕。
中彩票的风险无处不在
我去的时候正值寒假结束,机票还比较贵。为了省钱,我设计了两次换乘的路线。第一次,我的行李被检查通过了。第二次换航空公司,得自己取出行李转机。连接出发地、最终目的地和经停点的路线几乎是一个锐角三角形。如果算上第二次,它就是一个近似三角形的四边形。
虽然途中第二次转机断了,中途也换了航空公司,但差距还是蛮长的。根据我之前飞往美国的航班的良好印象,我应该可以转机。结果圣诞节前后,我发现美国出现了大规模取消延误航班的消息,尤其是达美航空飞往中国的航班原路返航。为了以防万一,我咬牙花钱买了稍后起飞的直飞航班。机票作为出境旅行的备用。
接下来是你们可能都看到的新闻:——。丹佛附近有一场暴风雪。哦对了,刚才忘了说了,我最初第一次转学的城市叫丹佛。
1月6日丹佛国际机场,此图来自社交媒体
我在恐惧中等了将近一个星期。我看到航班开始恢复的消息,以为不会有什么麻烦。然后我收到了订票网站发来的邮件:
说实话,如果我不需要继续转机,UA 给我的替代航班相当可靠,而且只向后推迟了几个小时。但我有后续航班不需要直接托运行李!检查后一切正常。不幸的是,第二趟转机机票很便宜,我无故取消了。看来没办法只能扔到水里了(后来发现航班因为其他原因取消了……)。
幸运的是,我是一个谨慎细致的人,善于确保自杀成功。备用的AA 票就派上用场了。原来的机票必须全额退款。幸运的是,两次退款申请都获得批准,钱也成功提取。
正如之前所说,我再次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放开了老同学。
但出发前一天,我还是去了现场(三分之一英亩,一个较大的针对北美华人和中国学生的论坛,有专门的疫情统计页面。),看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周一美国新增确诊病例高达141.9万例。 1月3日新增病例102.3万例,但元旦上班的人却很少。我看到的时候只是以为是因为假期期间确诊病例积压。然而,最近一周,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如果我这个时候是正常人,我肯定会放弃。如果我看不到你,我就看不到你。跑那么远,万一被感染了,那可就难受了。安全第一,待在家里,注意安全。
但我很快意识到这是美国,中国思维在这里根本行不通。
在此之前的倒数第二天晚上,独自在家躲了近两周的我(室友年底告别单身搬了出去)突然出现了新冠病毒疑似症状!
回想起来,一整天我都感到非常疲惫,直到下午才完全清醒。晚上失眠了(因为考试周熬夜的后果一直失眠,整晚都睡不着),所以一觉醒来迎接出发的最后一天。今天早上,我全身肌肉酸痛,身上出现很多小肿块,浑身出汗。用来操作电脑的鼠标上面有一层汗渍,必须用酒精棉擦干净。
由于没有发烧、呼吸道症状,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想到新型冠状病毒,就喝了一些抗病毒颗粒和连花清瘟颗粒。直到出现肌肉疼痛的症状,我才恍然大悟,一切皆有可能,于是我用了当时已经非常珍贵的iHealth COVID-19快速自检试剂盒,把检测液剥下来,倒了出来。放入试管中,然后将一根长棉签插入其中。浸泡、搅拌,然后将3 滴滴入看起来像验孕棒的测试窗口中.根本不会滴,我就拿了湿棉签在测试窗口用力擦了几下,导致液体到处都是。一分钟、两分钟、十五分钟过去了。测试溶液已经爬满了整张试纸,观察窗里只出现了一条线。消极的。
这是为了给朋友看的
好吧,所以我的身体还是干净的……但是疲劳和全身肌肉疼痛并没有改善。
我用很久以前买的指夹式血氧仪来测量指尖血氧。当第一次测量结果为94% 时,我感到震惊。第二次测量仍为99%,“完全正常”。
这张图是后来加上去的,是为了这篇文章做准备。它显示了我1 月20 日的手指氧气读数.
登机时间快到了,我的东西还没有收拾好。即使我停止收拾行李并去做PCR,我也无法在出发前看到结果。出于极其谨慎的考虑,我连续检测了四次,分别刺穿了喉咙和双鼻孔,把剩下的珍贵自检试剂盒全部吃光了。大约20分钟过去了,只剩下一条C线了。
排除操作技术等系统性误差,如果快速筛查的假阴性率为40%,那么如果Covid连续5次检测呈阴性,理论上不被感染的概率应该是98.976%。而且这个时候我发现两种中成药似乎起了作用,症状缓解了,疼痛也没有那么厉害了。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什么。这两种药本来是用来治疗普通感冒的。我给这位同学打了微信,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那边的同学。另一位同学很由衷地回答:“没关系,即使真的感染了COVID-19,也不用担心,只是感冒而已,完全接种疫苗的年轻人死亡概率为零。” ”现在还不是疫情初期。美国到处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携带病毒的人。还有人生病了去当医生给人治病,还有人生病了去日本韩国当兵……你失踪了吗?这一次,明天全美新增人口会少10万吗?而且你已经阴了五次了,你是太阴体了(我:……),你还想怎么样?最后我很体贴地告诉她,虽然我一点也不害怕被感染,但是一切都由我自己决定。如果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四处走动,这个计划就会被取消。
像我这样脸皮薄的人,总是会被朋友们的慷慨所打败。
想一想。即使是流感,流感和COVID-19的传播途径有不同吗?如果像我这样的模范自闭症孩子今年冬天能通过某种途径被感染的话【后来我严重怀疑是公寓的中央空调通风系统把病原体传给了我。如果是真的,那么无论新冠病毒还是流感,我都根本无法预防,那我为什么要预防呢?我只是戴个口罩什么的,只是为了安慰自己……】。那我为什么要出去呢?我应该害怕什么?没关系。寒假是我唯一可以离开家的假期。我在美国的寒假不多,不舒服就是不舒服。至于公共道德问题,根据我所在机场的规定,如果没有确诊、咳嗽、发烧等症状,就可以进入机场。我真的没有任何迹象。
于是安心决定像往常一样出去……我想问你,你敢不敢像我一样为爱情疯狂。
美国防疫模式下的机场和严格安检
尽管疲劳和肌肉疼痛,我还是收拾好行李出发了。虽然美国这里不太冷,冬天也没有雪,但我的目的地是在温暖的墨西哥湾旁边。一月最高气温28.8度,要带一套专门的夏装;我本来带了一套秋冬的衣服,是室内用的。出发的时候,我担心带不动,就把衬衫留在家里,只带了裤子。他身上穿的工作服原计划是防护服,到达当地后就会被扔掉。我抓起半盒KN95口罩,出发前两个小时,像吃糖果一样吞下了一整块连花清瘟胶囊和两包抗病毒颗粒。我还又买了几包在中国超市的食品区买的。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清肺排毒汤颗粒是真还是假?背上书包,出发吧!
在美国购买了该产品。中国人在海外做生意总是让我感到震惊,但相比那些敢于公然出售抗生素的商店——别问我是哪一家,我去学校公厕听了隔壁的坑【注:本文不是一篇科学论文,有些部分是次要的。细节严谨程度仅供参考。 ]——这根本不算什么
我提前办理了登机手续,打印了登机牌,办理登机手续时询问了优先通道。这件事检查和告知同学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机场早期的。想想美国的疫情数量与日俱增,像我这样固执的人应该不多了。机场应该是一片洼地,我就在登机口旁边浪费一个小时。 —— 买票选座时,几乎没有空位。我早已忘记这件事了。
结果呢?结果,我已经在值机大厅看到了不祥的征兆。 ——人太多了。一坐自动扶梯上楼,亲爱的,五羊五羊小小的安检区就挤满了人。
进入安检区前,我把驾照交给了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他皱着眉头看着还戴着口罩的我,说道:“把口罩摘下来。”
事情就是这样完成的。
他说:“看我的左边。——别低头,放松肌肉,——别紧张,喘口气!”
事情就是这样完成的。
嘟嘟的一声,他把驾照交还给我,我面无表情地放回口袋,然后在人海中重新戴上KN95口罩。
我是在回来的路上才决定写这篇投诉的,所以我不能谈论这些事情。我只是在出发的时候有空在登机口拍了几张照片。下面的照片是在回程机场拍的,但去程机场的场景一模一样。
地板上有“社交距离”线,但根本没有社交距离。现场有管理人员准备向没有口罩的人免费发放口罩。然而,机场、航空公司或运输安全管理局(TSA)都没有试图要求乘客按照地面上的“社交距离”线站立;排队的人太多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安检处排队等了40分钟。 40分钟内有多少人进来?看不清,好像只有几十人。但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来证明安全检查的严格性:
自从来美国后,我就一直随身携带两支Saber式防狼喷雾剂。一种是小的,看起来对人畜无害,看起来像口红,另一种是大的黑色1.5盎司警用定向强力版。它结构紧凑,但非常坚固,可以在最远5.5米的范围内准确发射具有标记效果的催泪瓦斯凝胶,而不伤害封闭空间内的其他人。但自从来到美国后,并没有发生任何让它们有用的事情,所以最近一两个月我就忘记了它们。
左边那个被我“背叛”了,壮烈牺牲了,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这是我后来找到的产品的图片。
正如之前提到的,我在出发前的最后两天生病了。登机当天,我忘记从随身携带的两个行李中取出它们,并把它们都带进了机场;我不得不排队等待40分钟。当我到达安检口,收到箱子时,我正准备从包里拿出所有的电子产品和金属鞋,倒进去。当我打开包时,我立即想起了小喷雾剂的存在,并在TSA 安检员面前直接将其取出。 ……我只好假装听不懂,天真地问道:“我可以带这个吗?”
结果安检人员一看就问我:这是什么?嗯,这东西看起来确实太像口红了。我愣愣地解释了十秒钟,差点就得当场给她演示了。让她明白。当然我被告知不能带。于是她打电话给另一名运输安全管理局官员寻求支持。两人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大概是专门用来装炸药的圆盘状小容器,将那支可怜的小口红塞进去,用了一把。这个小容器被用钳子之类的东西抓住并以非常专业的方式取出。
安检排队区混乱拥挤。这张照片也是回程时拍的。只是看起来很拥挤。
于是我继续拿出电子产品,脱掉外套(用作防护服的破烂长袍),脱掉鞋子,穿过安检门,走向对面的传送带。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我的东西寄出去。我一看手机,距离登机牌上的登机停止时间只剩下7分钟了。我赶紧把外套穿回身上,把东西抓回书包里。他不顾全身的疼痛,将书包和书包扔回肩上,朝另一座航站楼的登机口跑去。口鼻被密闭的KN95口罩遮住,跑了几步就感觉窒息。想到自己消耗了四不五根珍贵的验孕棒换来的新冠病毒阴性结论,我果断地面对了人群。在机场值机区,他像东海岸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一样摘下了口罩,一边奔跑一边自由地呼吸着美国机场的空气。
还是太晚了。
还剩3分多钟了。我戴着口罩,呼吸粗重,浑身酸痛,眼睛被汗水刺瞎,背着书包和沉甸甸的书包;看来我还有将近一公里的路要走。难道是因为“低估了美国人尽管疫情下的旅行欲望”的错误,才导致一次旅行一开始就以如此尴尬的方式结束?一度想当场突破防御停下来,然后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用力摇头几次才能平静下来。根据这几天美国的延误情况,估计我的航班也会延误,所以或许还有希望。但如果只是晚了几分钟,不抓紧时间就会错过。
于是我还是强忍着不适,继续以最快的速度跑向原来的登机口。
果然,尽管我到达登机口时看起来像是从密西西比河中捞出来的,但我仍然比登机牌上打印的截止时间多了三分钟。幸运的是,飞机确实延误了,登机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根本没有开始。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小喷雾在小包里的话,那么大喷雾很可能还塞在书包侧面的网兜里。我伸手一抓,就有一种熟悉的安全感……美国安检,好吧。
登机口人山人海、酷暑难耐,几乎和中国的春运一样。好家伙,这和新增确诊110万例后的第二天完全不一样。但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考虑到我所到之处的人均持枪人数,既然上帝赋予了我自卫的权利,我就不能把接下来几十个小时的命运寄托在当地淳朴的民风上。 “不予采纳”的标志太明显了。繁荣、快速发展的美国社会早已把我培养成了一个习惯于照顾自己的精神共和党人,并认为这至少是我在美国期间所珍视的基本价值观。
飞机起飞仅延误了约20分钟,正好赶上办理登机手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一切都很顺利,顺利登机、飞走。
我在狭窄的中间座位上睡得很香,这个座位既不靠近窗户,也不靠近过道。我什至想念服务员分发食物和饮料。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旁边那个好心的白人向我要食物。长条上只有一小块饼干。或许不用摘下口罩,从下面塞进去比较方便吧?出色地……
疫情期间所有美国航空的机上餐食
虽然饼干的外包装被两名无绿码、近距离接触概率较高的高风险地区人员触摸过,但他们已经赤裸着嘴巴和鼻子,在人群中裸奔了。他们应该害怕什么?没有生病,我抓住它,把它撕开,整块吞下去。想着不能白来了,就把剩下的那一块拍了一张,然后吞了下去,又回去睡觉了。
剩下的飞行很顺利。一下飞机,周围人都快空了的时候,我就养成了死的习惯,把一罐警用喷雾剂放在靠窗的座位上,拍了张照片留作纪念,然后就离开了。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走了
由于时差的原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机场外白雾缭绕,但我穿着衬衫却丝毫不觉得冷。我只觉得书包沉甸甸的。一路上,我找到了一家提前订好的酒店(疫情期间不可能住在同学家,虽然随意,但我还是有一点节操的)。我按照计划把那件沾满了无数空气飞沫的袍子扔进了垃圾桶,并对自己说了一次去污行动。不管是什么病,几十年后他就会死。将一盘连花清瘟胶囊与健怡可乐一起吞下。
本来想看看明天想去的景点,但是全身真的好痛。我想明天没有时间再补一下。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倒在床上,然后呢?我不知道了。
胜利逃脱
我从阿拉巴马州来,带着我心爱的班卓琴,去路易斯安那州寻找我的爱人。我们是傍晚出发的,雨一直下个不停。天气真的很干燥,太阳当空。我的心很冷。苏珊娜,别哭。哦,苏珊娜,你会为我哭泣吗?
我来自阿拉巴马州
带上你最喜欢的班卓琴。嘿!
在美国再次展开拯救全人类的伟大壮举,航天飞机和大量导弹即将返回之前,我点了点鼠标,关掉了Netflix的《Don’t Look Up》。
突然我发现,我住的地方似乎离电影中的发射场不远……看不见,但并非遥不可及。如果租车的话,开不了多久就到了。
一瞬间,我有一种差点见证历史的遗憾。
在COVID-19病例每天以数十万的速度增长的美国,两个自杀小高手如约在市中心一家昂贵的夏威夷餐厅吃饭。我们彼此诚实,如我们所愿的纯洁;我们聊着爬长城的岁月,抱怨着一年前覆盖南方的暴风雪和停电,聊着本来可以通过视频通话重述的往事,然后戴上KN95口罩挥舞着衣袖然后离开。
哦,顺便说一句,让我补充另一个细节。为了互相保护,我们斜对面坐着:
灵魂画师——我
该玩的地方都已经被引导去玩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因为各种原因打开了面具。反正把戴口罩当成一种仪式就好了,回到学校也是一样。
是时候快点回去了。这些天,不仅我小小的身体勇敢地坚持了下来,而且出发当天在出发大厅剧烈运动所流的汗似乎也治愈了我的病。虽然我的四肢还很无力,浑身酸痛,但大部分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但这并没有发生,手指的氧气仍然保持在极高的水平。
一位朋友建议我在当地做一次免费的PCR。我想了想,决定忘记它。如果我的检测呈阳性怎么办?不被隔离是不合理的,而在知道自己呈阳性(即使是假阳性)的情况下登上飞机并飞走将更加不道德。但如果我因此而主动就地隔离14天,这个社会谁来报销我这14天的隔离费用,帮我向系里请求推迟注册开学14天.
所以我没有测试。我没有对社会上所有陌生人的健康承担最大的责任。在这个亚裔无罪就容易被打的时代,我承认我简直犯下了损害亚裔美国人在美国声誉的罪行。然而,在这个据说已经从疫情阴影中走出来、开始从“与病毒共存”中恢复过来的社会里,像我这样经济状况的人,很难比我更有道德了。如果我不幸参与了病毒的传播,我就会犯下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深夜,我突然梦到了少年时的事……
我的朋友坚持直接开车送我去机场,但我拒绝了。反正我冒险出去了,身体也没有太难受。我打算最后一天独自在城里走走。 —— 我的内心深处一直住着一个叫做“流浪癖”的恶魔。对死亡的恐惧让我在美国抗拒了魔鬼的召唤一年。最后,在另一个叫“友谊”的恶魔的号召下,我放弃了治疗。
就这样,我一个人在街上闲逛,逛着商店,手机上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几个小时后我的回程航班被取消了。
这次旅行难道就没有一个航班可以让人省心吗……
我赶紧回酒店拿书包。过了一会儿,我收到了一封新电子邮件。航空公司给我安排了另一趟航班。一天后它将出发。我会先飞到芝加哥,等待四个小时,然后换乘另一架飞机,通过直接值机将行李转回原定抵达机场。在美国地图上走一条近150度的大折线。
芝加哥?我没有为这么北方的地方准备衣服!
他看着自己清凉的夏装。我打开书包,发现除了一件单薄的衬衫,我唯一的冬衣就是裤子。我后悔没有带秋冬外套,因为它太重了,我后悔来到这里时把用作防护服的上衣扔掉了。我拿出手机查看。芝加哥夜间最低气温为8 华氏度(零下14 摄氏度)。即使我不离开机场,下一趟航班不延误,我也可能会在四个小时后被冻死。 —— 我还在生病。它得到了对预算有限的旅行的顽强渴望的支持。
我学习的地方不是大城市,但确实是大城市,但不能说是航空枢纽。我搜索了第二天的直飞航班,但没有找到。甚至第三天也没有。第四天,还有……好吧,我的预算实在是住不起酒店多住三天了。在机场睡觉?以我正常的身体,在机场睡一晚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连冒险都不敢,更别说在机场睡两晚了。后天就开学了。
这次是美国城市发展的均衡水平救了我。我联系了一位朋友,多次拒绝他的过夜要求后,我得知我们城市旁边的另一个城市的航空业很发达,那里可能有直飞航班。我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果然有很多直飞的航班。我立即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要求他们更改我改签的机票的出发点。花了很长时间才打通,谈判失败后,他们坚持要我换。航班只能从原定地点出发。你们正在编织呢!我半夜要开车去这个地方,所以我没有麻烦朋友载我一程。我果断花了钱,买了第二天早上从航空枢纽城市返回所在地的机票,然后订了晚上出发的航班。巴士票,整夜奔向我下一次救生航班的出发点。
长话短说,我是半夜到达那个城市的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过安检,提前半晚到达指定登机口。这次转会打破了我最近一次在美国走动的记录。那还是一个人均拥有民兵的共和党州,也是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幸运的是,一切都很顺利。 —— 对了,忘了说了,大浪花又进了我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中我忘了提前扔掉,然后就跟着我通过了安检,进入了登机区。我向上帝发誓,这一次真的是一个无心之失。这绝对不是故意的。啊啊……
这是我发到微信朋友圈时拍的照片。我还是害怕晚上的值机柜台。
这时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写这篇投诉信了。半夜,我喝了几瓶咖啡,强忍着不适。熬了一夜,仿佛命运认为我此行遇到的惊喜还不够,高潮来了:——,飞机没有来。
附近的座位挤满了等待航班的乘客
等飞机的几个小时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长椅上发呆,打瞌睡。中间只起身去厕所,假装玩手机,像小偷一样看着登机口坐着的人。拍了一张照片。所以整个过程没什么可记录的,所以我把我最后上飞机时的邮箱地址截图贴在这里。您可以欣赏图片并表达您的感受:
向我展示航空公司如何盗取我的Microsoft 365 邮箱
上飞机后,我询问了坐在我旁边的女士,得知延误的原因是飞机上的厕所全部坏了。机长要求地勤人员至少修理其中两架。事实上,直到起飞时才意识到。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整个过程中我根本没想过要上厕所。
如果我在公共汽车、轮船或飞机上都无法控制住它,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回程航班上的食物是一样的。这次不要错过饮料,再拍一张照片。一共点了两杯饮料,第一次点的咖啡还没来得及拍照就一口气喝完了。不然你会立刻睡着。
我第一次点了一杯含糖的普通可乐。这块手指那么大的小饼干给我提供的能量不足。我已经将近二十个小时没有吃喝了。
感谢美国航空的空姐,她真的很友善,主动警告我坐在我后面的乘客一直摇动我的椅子。
正如你所看到的,回程几乎不伦不类,因为我仍然处于半昏迷状态,尽管我仍然喝太多咖啡而无法入睡,所以我没有忘记行李架上有一个书包。到了车站,下车,哦不,下了飞机,叫了Uber,把手放到了一路陪伴我的警用胡椒喷雾瓶上,强迫自己一路保持清醒到火车站,跳上下一趟火车,到达。停下来,叫Uber,把手放在喷雾瓶上,看着司机一路清醒到小区门口,哦,到家了!甜蜜的家……
该照片是作者之前拍摄的,并不是新照片。
后记
截至发稿,回国后进行的PCR检测结果为阴性。想想,我就可以放下“平庸之恶”的心理包袱了。然而,这次旅行,我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主动和被动地打开口罩的次数太多了。我无法预测我是否会赢得别人的大奖,或者PCR检测结果是否会是假的。消极的。更何况,作为一个爱找死又怕死、善于吓自己的中国留学生,他似乎还是很容易疲倦、昏昏欲睡、肌肉酸痛……总之就是各种不想努力学习的借口现在可以解释为疑似感染了COVID-19 的症状.
好消息是,由于新一波感染扰乱了学年的重新开放,学校的实体课程已再次暂时关闭。所以不用担心逃课。在下月初之前,您应该继续处于合法的自闭症状态。
并且,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在异国他乡,我衷心感谢对方冒着生命危险给予我这样的盛情款待。学年开始时,朋友们应该立即进行强制性PCR 检测。我希望结果是阴性,一切正常。
就像A姐在《不要抬头》中唱的那样,“抬头看!/快到了,/我真的很高兴这个时候有你在我身边……”
综上所述:
首先,我此行还不足以得出“美国民航秩序因疫情爆发”的结论。我应该算比较不幸的,一切都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然而,美国民航的防疫工作确实进入了执法与实际操作完全脱节的状态,这在这个国家是罕见的。
各级官方部门和企业的宣传力度依然不减,甚至以防疫为卖点。美国航空在广播中打出广告:“我们每次都会对机舱进行医院级别的消毒……”——看着色彩鲜艳的座椅和地毯。我来自中国,我知道“医院级消毒”。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需要说明的是,大家只是在假装预防疫情,给自己增添一些麻烦,在这个巨大的感染链中推卸自己的心理责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人愿意刺破这层窗户纸。
其次,美国民航业并未陷入萧条;相反,它(也许在混乱中)正在经历令人难以置信的繁荣。但代价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国后疫情时代出现经济起飞,那将是“把无法抵抗病毒的弱势群体扔下飞机”的达尔文式起飞。亲爱的读者,如果你因为文章中的种种行为指责我在中国无所畏惧,那么我只能说,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负责揭发的媒体以及包括我在内的人民,那些被胁迫的人。全社会共同在“把防疫生活自由放在第一位”和“确保个人免于恐惧”之间选择了前者,在“小人物的尊严”和大国的GDP之间选择了后者。
也许这就是另一种平庸的罪恶。
虽然这是中国制造的,但我希望我家乡的父母永远没有机会自己学习使用它们。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天阅读有趣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