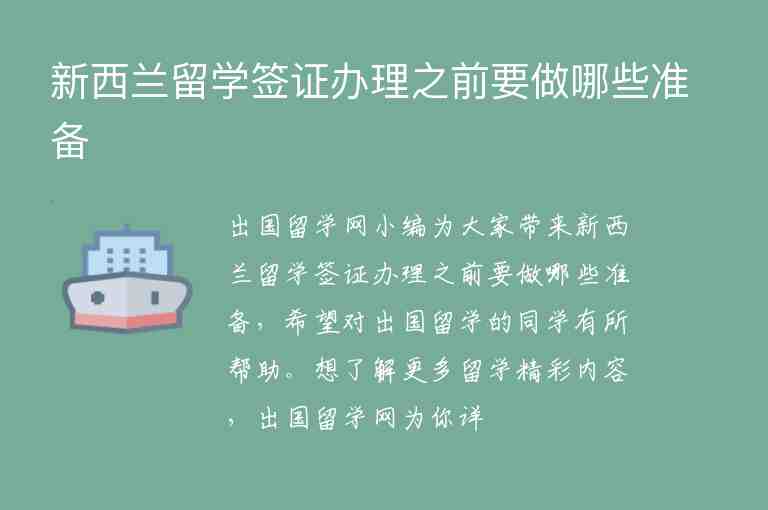随着《魔女嘉莉》(史蒂芬·金)》、《魔女宅急便》等流行文化作品在全世界传播,女巫正逐渐褪去污名化的外衣,成为一种标榜反抗和自由的文化。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女巫集会”(covens)就在纽约等多个城市诞生。她们大声喊出自己的心声:女巫一直是敢于勇敢、积极、聪明、不墨守成规、好奇、独立、性自由、革命性的女性……女巫在每个女人身上都活生生、欢笑。她是我们每个人自由的部分……只要你是一个叛逆、愤怒、快乐、不朽的女人,那么你就是一个女巫。
但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女巫一般与阴谋、恐惧、血腥、迫害、火刑柱等联系在一起,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枷锁下对女性的一种诽谤、侮辱、剥削和压迫。托马斯·曼认为,文化与各种可怕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秩序、魔法、鸡奸、活人献祭、邪教狂欢、宗教裁判所和女巫审判等等,但这些都被文明所拒绝。文明是理性、启蒙、节制、礼仪、怀疑、感性的解构。从托马斯·曼等文化巨头的观察来看,女巫审判是违背文明的。然而,对女性的恐惧导致这种现象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300年里不断重复,有数十万女性在政治迫害中惨死。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而政治迫害背后的动机尤其值得深思。
如今,在被视为现代文明核心的欧美,以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欠发达地区,对妇女的谋杀并未停止,猎巫的声音仍在高涨。先后。正如阿瑟·米勒在他的剧作《哈利波特》中所说:性、罪恶和魔鬼早已勾结在一起,所以它们继续存在于塞勒姆,并继续存在于今天。意大利学者、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活动家、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名誉教授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的著作涉及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向我们阐释了猎巫的深刻含义:从多个角度来看一种政治迫害和文化现象。我们的世界是否因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美好?费德里奇回应道,引用了一位来自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女性的话:“在我们看来,你们的进步历史就是一部剥削历史。”
被忽视的东西
Federic的《萨勒姆的女巫》研究主题是关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女性。从女性、身体、原始积累的角度重新审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揭开那些被忽视的伤痕。开创性地将欧洲猎巫运动与猎巫全球化相结合,重新审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土地私有化和商品化阶段,无产阶级特别是妇女在劳动再生产过程中所遭受的残酷和剥削。社会关系。这恰恰是马克思忽略的部分。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在重商主义、天才世纪、机械唯物主义和启蒙运动的背景下,科学家、哲学家、法官和统治者合谋完成了对女巫的谋杀,并将其提升到了政治地位。运动、一切厌女症、猎巫,都是为了促进资本积累和殖民扩张。费代里奇还从历史、哲学、文化史、甚至艺术和科学的演变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失去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无理迫害。这是一部理解女性和女权主义的杰作。
《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
费德里奇敏锐地指出,在中世纪,女性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在无产阶级诞生的过程中,妇女也是争取独立和领导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公地的社会功能对于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她们拥有的土地较少,社会权力也较少,她们的生存、自主性和社会性更多地依赖于公地。前资本主义欧洲市场对女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公地是妇女社交生活的中心。这是他们举行会议、交换消息、听取意见的地方。在这里,女性可以对社会事件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依赖它们。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在反抗斗争中,妇女斗争的印记随处可见。例如,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女性参与了大约10%的圈地骚乱,有些甚至是完全由女性发起的抗议活动。
马克思认为,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前的关键阶段,涉及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向资本的转化。这一过程以剥夺农民土地为基础,促使直接生产者转变为雇佣工人,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原始积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本质特征。
德国社会学家玛丽亚·密斯也将其列入20世纪最重要的100本社会学书籍之列,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著作之一。强调:“家庭主妇和她的劳动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基础。” “女性是资本最廉价的劳动力,她们被视为殖民地和自然人。”
《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是指物质材料生产的重复和扩大。核心是资本家利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利润。这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关系的延续和加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本质是资本家追求无限的利润,导致生产的扩大和对工人的剥削加剧。
费代里奇对此进行了反思:恩格斯在《第二性》(1884)中提到的历史失败是母系世界衰落的原因。因为政治迫害摧毁了整个世界的女性实践、集体关系和知识体系。这是前资本主义欧洲妇女权力的基础,也是她们反抗封建斗争的条件。从这次失败中诞生了一种新的女性模式,即理想的女性和妻子是被动的、顺从的、节俭的、沉默寡言的、总是忙于工作的、贞洁的。
费德里奇比玛丽亚·密斯更进一步,认为马克思所忽视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将妇女的“压迫”和对男性的从属解释为封建关系的残余。妇女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一直是剥削工资劳动者的基础,被称为“工资奴隶制”,也是其生产力的秘密。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男女的权力差异并不是因为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积累无关,也不是因为永恒的文化制度。相反,它应该被解释为社会生产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不承认工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和资本积累的源泉。相反,这个系统将其神秘化,将其视为自然资源或个人服务,同时从这个过程中的无偿劳动中获利。
猎巫运动与新大陆的殖民和灭绝、英国的圈地运动、奴隶贸易的开始、针对流浪者和乞丐的“血腥法律”的颁布、封建主义的结束和“掠夺”的发生同时发生。资本主义的“关闭”时期达到了顶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局限性在于她们未能认识到再生产领域是价值创造和剥削的源泉。
通过惩罚女巫,统治者惩罚了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对社会的不服从、被认为拥有超出他们控制能力的魔法信仰的传播,以及对性规范的偏离,并在国家统治下取代了这些规范。性行为和生殖。从而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再生产。这是马克思所忽视的真理,而费代里奇则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对原始积累理解缺失的重要部分。
卡利班和西考拉克斯被玷污
被誉为电影天才的英国大导演德里克·贾曼改编自莎士比亚名剧《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的影片中,卡利班被塑造成一个贪婪、任性、口是心非的奴隶,主角普洛斯彼罗正在斥责他。当心怀不忠的精灵爱丽儿出现在场景中时,平时隐藏在幕后的女巫形象通过倒叙的方式被带了出来。西科拉克斯(Sycorax),卡利班的母亲,肥胖、肉欲、肮脏、暴力且充满邪恶。贾曼的电影视角反映了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即卡利班和西科拉克斯继续以邪恶的形象出现,而不是殖民时代的受害者和父权制目光下的污名化人物。
德里克·贾曼导演的电影《父权制与资本积累:父权制与资本积累》 海报
西科拉克斯的巫术和普洛斯彼罗的魔法都是同类的暴力手段。后者一边诽谤、诽谤前者,一边为自己的魔法辩护。全剧中西科拉克斯的缺席以及普洛斯彼罗对其形象的再现,可以更好地洞察普洛斯彼罗的殖民心态,揭示他在殖民时代所代表的性别殖民话语,并揭示他的殖民者的霸权。自然。
普洛斯彼罗凭借话语霸权完全掌控了西科拉克斯的形象塑造。对于普洛斯彼罗来说,边缘化西科拉克斯形象的第一步就是将他的魔法与女巫的巫术区分开来,以证明他的魔法是向善的,而后者的巫术是向善的。艺术是邪恶的。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原文中得到了加强:
普洛斯彼罗:你撒谎,你这个恶棍!那个邪恶的女巫西科拉克斯—— 她因为年老而心肠邪恶,弯得像戒指一样—— 你忘记她了吗?
爱丽儿:不,主人。
普洛斯彼罗:你一定忘记了。她出生在哪里?到我这里来。
爱丽儿:在阿尔及尔,大人。
普洛斯彼罗:哦!是在阿尔及尔吗?我必须每个月告诉你一次你的出身,因为你一下子就忘记了。邪恶的女巫西科拉克斯(Sycorax)被驱逐出阿尔及尔,因为她做了如此多的恶行,以致没有人能听到或害怕她的魔法;他们没有杀她,因为她做了一些善事。是还是不是?
爱丽儿:是的,主人。
普洛斯彼罗:这个蓝眼睛的妖妇被带到这里时已经怀孕了;水手们把她遗弃在这个岛上。你,我的奴隶,据你自己的说法,当时是她的仆人,因为你是一个过于温柔的精灵,无法服从她严厉而邪恶的命令,因此违背了她的意愿,而她一怒之下,借用了在她强大的恶魔奴隶的帮助下,她将你囚禁在一棵裂开的松树中。你在松树缝里度过了十二个悲惨的岁月;然后她就死了,而你却留在那里,不断地发出呻吟声,就像水车搅动水一样迅速而持续。那时,岛上除了她生下的儿子,一个长满痣的女巫和母狗外,没有任何人类。
爱丽儿:是的,那是她的儿子卡利班。
普洛斯彼罗:那个卡利班是个傻瓜,现在我把他当作奴隶。你当然很清楚,当我发现你在遭受怎样的痛苦时,你的呻吟让豺狼嚎叫,你的哀鸣刺痛了愤怒的熊的心。这是一种导致永恒诅咒的痛苦。即使是Sycorax 也无法释放你。后来,当我到达岛上,听到你的哭声时,我用魔法在松树上打开了一条裂缝,杀死了你。释放。
普洛斯彼罗以话语霸权的形式完成了对爱丽儿的控制和驯化。艾瑞尔只能回答“是”和“否”,而西科拉克斯则被固化为“心地邪恶”和“作恶多端”。完全符合民间传说中的女巫形象,对她的污名化在这一刻完成。
费德里奇认为:卡利班不仅代表了反殖民叛逆者的斗争,其斗争至今仍在加勒比当代文学中回响,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象征。更具体地说,他将无产阶级身体象征为抵抗资本主义逻辑的场所和工具。
《暴风雨》 中女巫的Sycorax 人物最初仅限于遥远的背景,而本书将其置于舞台中心。她体现了资本主义必须消灭的女性主体世界:异教徒、治疗师、不听话的妻子、敢于独居的女人、在主人的食物中下毒并煽动奴隶反抗的奥比女巫。
对女性的恐惧仍在继续
Federici的《暴风雨》是对《暴风雨》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它梳理19世纪至今,聚焦资本积累的新形式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猎巫运动,从国际化和历史的角度关注全球化和全球化。对女性的暴力如何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愈演愈烈,折射出科技影响下女性的困境。
《暴风雨》
费德里奇强调:在当今全球化和资本重新积累的过程中,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特别是针对非裔和美洲原住民妇女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因为“全球化”是一个政治再殖民化的过程。其目的是让资本对世界自然财富和劳动力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如果不攻击妇女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妇女对社区的再生产负有直接责任。毫不奇怪,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更加严重,这些地区现在是商业投资的焦点,同时,这些地区也成为了反殖民主义的中心。该地区的斗争也是最激烈的。对妇女的残害对于“新圈地”来说是切实可行的,这为多年来蹂躏整个地区的土地掠夺、私有化和战争铺平了道路。
对于医学进步带来的对女性新的剥削形式,费代里奇指出:对女性的攻击一般源于资本需要摧毁其无法控制的东西,贬低其自身繁衍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女性的身体,因为即使在超级自动化的时代,如果没有怀孕,就不可能工作或分娩。体外受精并不存在。我们必须拒绝这种话语配置。这是男性对女性体外受孕的探索。这也是资本尚未攻克的新领域之一。
更残酷的是,出售器官和身体部位用于移植或用于某些仪式以获取财富的现象正在非洲蔓延,引起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恐惧,认为邪恶势力正在吞噬人们的生命。能源和人文。对巫术的指控,就像非洲殖民地的吸血鬼故事一样,可以被视为对生活商品化的回应,资本主义不仅寻求重新激活奴隶劳动,而且将人体本身变成资本积累的手段。
资本主义对女性的恐惧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只要威胁到资本建立的统治秩序和利益崛起的道路,女性就会被用作威胁社会秩序、损害经济利益的替罪羊。
身体控制之战永无休止
在法国女权主义动画连续剧《对女性的恐惧:女巫、猎巫和妇女》中,探讨了这个话题:在所有女性卫生巾/卫生棉条的广告中,月经都被蓝色液体取代。好莱坞巨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表示:我从不与25岁以上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凯列班与女巫》 在这类流行的情色小说中,作者有一种固化的父权观念驱动着他的创作原则,即女性应该受到惩罚,因为女性是自卑的,动机充满了强烈的厌女症。消费主义和父权制塑造了苗条的美学。女人总是处于自我怀疑之中,质疑自己是否美丽或足够优秀。在极度减肥的情况下,卵巢不再产生卵子。
正如费德里奇所说:我们拒绝被分为美丽和丑陋,我们拒绝遵循强加给我们的最新的美丽模板,而遵循这些模板往往需要我们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来进行痛苦的节食。不仅如此,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就像黑人权力的兴起一样,美也被重新定义。我们欣赏彼此的美丽,因为我们是叛逆者,因为在将自己从厌恶女性的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新的存在方式,新的笑方式,拥抱,梳理头发,交叉双腿的方式,新的相处方式和做爱。
在《对女性的恐惧:女巫、猎巫和妇女》年间,费代里奇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科学等各个方面对身体政治和身体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对医美、代孕等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剥削,以及当前人工智能乃至未来太空探索中资本主义对女性的规训和迫害有着精辟的见解。其丰富的妇女运动斗争经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堪称实践出真知的典范。
《自由的她们 Libres!》
在现代女性面临的身体控制权斗争中,更为突出的是职场性侵、性骚扰、堕胎自由等较为敏感的话题。费德里克在《五十度灰》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女权运动不能为确保任何妇女因生活的物质条件而被剥夺生育的权利而奋斗。女权主义者将堕胎视为一种“选择”,这在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之间造成了分歧。我们看到类似的动态,因为许多女性一次又一次地未能认识到性暴力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变态男人滥用权力。说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被迫生活的经济条件为妇女遭受性虐待创造了条件。显然,如果女性能够赚取更高的工资,如果女服务员可以在不依赖小费的情况下支付房租,如果电影导演和制片人无法决定来找他们工作的年轻女性的未来,如果我们可以摆脱虐待关系,或者只有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性骚扰我们能看到改变吗?
作为西方女性第三波浪潮的旗手,朱迪思·巴特勒在其代表作《超越身体边界》中指出,对于波伏瓦和维蒂格来说,将女性与“性/性别”等同起来是一个错误。将女性这一范畴与其身体的外在性化混为一谈,就是剥夺女性的自由和自主权,就好像这些是男性的权利一样。因此,要打破性/性别的范畴,就必须摧毁一个属性:性/性别;通过厌恶女性的提喻,性别属性凌驾于自我决定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之上。地点。也就是说,只有男性才是“人”,除了女性之外没有其他性别……
《超越身体边界》
巴特勒还强调,性别认同是通过社交互动的表现来构建的。个人通过模仿和符合社会期望的性别角色来表现自己的性别认同。这种表演性意味着性别认同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随着情况和互动的变化而变化。
Federic在《超越身体边界》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首先,表演让我们非自然化“女性气质”。它扩展了我们对性别认同和价值的社会建构本质的理解,但它不允许我们承认,要引起社会或性别的变化,我们不仅需要改变我们个人和集体对性别的看法;还需要改变我们对性别的看法。首先改变性别关系赖以维系的制度的是社会通过贬低生殖工作而建立起来的性别分工和等级制度。其次,表演使社会行动的内容扁平化。它假设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同意或不同意,从而低估了许多同意行为中酝酿的叛乱。我们反抗制度,暗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活动,在某些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强大机构用来囚禁女性及其身体的牢笼。社会身份并不是女性不能撕下、翻倒或扔掉的一件外衣。相信社会身份是单方面构建的,忽视了女性改变社会身份的能力。那么对于身体控制权的争夺将会继续下去。
不同观点,值得商榷的费德里奇
当然,费德里奇并不完美。她的著作和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但史实和史料运用中的一些问题仍然值得讨论。例如,《性别麻烦》中最引人注目的主张:在几个欧洲国家,数十万妇女被审判、折磨、活活烧死或绞死。他们被指控向魔鬼出卖身体和灵魂,通过魔法手段谋杀了数十名儿童,吸他们的血,用他们的肉制作药剂,导致邻居死亡,毁坏牲畜和庄稼,引发风暴,等等。
牛津万圣学院资深学者罗宾·布里格斯(Robin Briggs)在他的《性别麻烦》中提出了更为严谨的数据:在女权主义兴起和巫术潮流的背景下,一个相当诱人的传说开始流行,认为900万女性在欧洲作为女巫被烧死。 ——不是种族灭绝,而是“性别屠杀”。这是一个高估,使实际数字增加了一倍200,因为现在最令人信服的估计表明,在1450 年至1750 年间,可能进行了100,000 次审判,也许有40,000 至50,000 人被处决死刑,其中20% 至25%被处决的是男性。
《超越身体边界》
布里奇斯将巫术问题的讨论置于更全面的历史背景中,并广泛地从巫术审判的证词和文献中的解释中寻找答案。他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深刻理解带入了现代。对早期西欧和新英格兰地区所有巫术案例的社会背景的综合分析和综合审视,使问题的解释更加令人信服。
《国际共产主义杂志1919》网站上有一篇题字《凯列班与女巫》(卡利班与女巫:批判性分析)严肃的书评文章,误用了费德里希书中的历史和事实,处理图片素材和信息来源等使用创造性和发人深省的方法。这些更好地让我们从更理性、批判性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待费德里奇和她的理论。
费代里奇曾感叹:我们是女佣、妓女、护士、精神科医生。这就是“母亲节”被歌颂的“英雄”妻子们的精髓。我们大声疾呼:停止庆祝我们的剥削和所谓的英雄主义。被忽视的伤痕深深地伤害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无产阶级女性。然而,阳光总能冲破浓浓的黑暗。 2024年国际妇女节,法国巴黎旺多姆广场,在庄严的司法部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高喊:这是“法国的骄傲”!堕胎自由已写入法律。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宪法上保护妇女终止妊娠权利的国家。性别平等的道路还很漫长,对女性的恐惧和迫害依然每天都在发生,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参与到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中。我们的世界永远会踏上一天天进步的征程,我们应该越来越坚定地等待着女性枷锁被粉碎的那一天,一个新的世界已经站在了我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