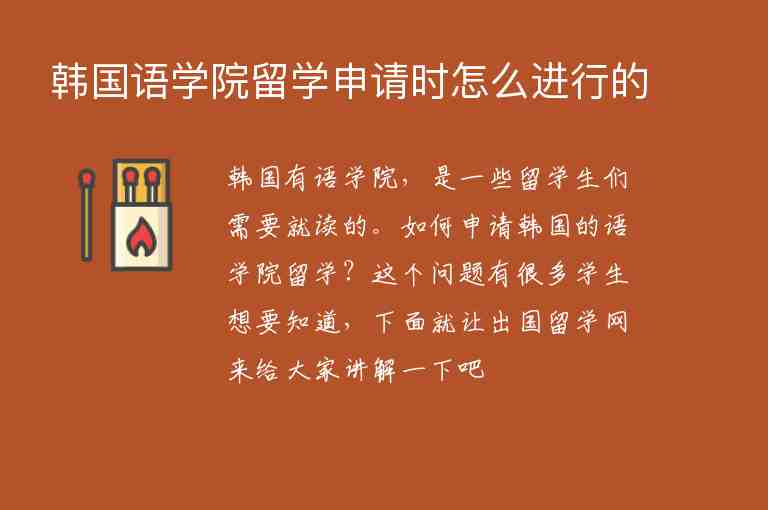闹鬼, 利兹
我正在洗澡,接到珊的电话,耳边响起她的声音:你信吗?我的地方闹鬼。
我当然相信,我们都是会遇到这种事的人。一年前我来到利兹留学,希望获得美术学位,然后我认识了我的同学单和黄磷。我们三人因疏离和贫穷一拍即合,互相鼓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功课已经快完成了,每一天,我们都在彼此的纵容下变得更加闲散。
白天,单某在一家餐馆做临时工。晚上,我们沿着城市边缘的运河散步。当午夜到来时,一支业余轮滑队就会在整个城市的地形差异中呼啸而下。后来,珊就走了。我正在和一个来自塞尔维亚的人约会。第二天一早我回到家,我和黄粉就在她家等她,因为我们无处可去。单背对着我们,把假睫毛粘在桌子后面。旁边那一簇,每次我都忘记见过多少次班仔了,只是用指尖摩擦数数。
在一起的时间很多,聊天的时间也很多。 Shan总是问问题,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当我们无法回答时,她会把所有湿裙子塞进手提箱,跑到南欧的伊维萨岛寻找新鲜的。麻烦。至于黄婆,他总是讲故事,重复故事,讲他来英国之前那些疯狂的前女友,以及她们的狂热如何让他害怕和尴尬。最令他自豪的是:
黄佛曾经有过一个残疾的女朋友。她的一只脚瘸了,走路就像指南针一样。分手那天,她一脚跟着他转了一圈(黄婆总是这么说,站起来模仿),他在几步外等她,脑子里写着分手对话,光标等待的输入随着她身体的节奏而闪烁。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脸已经被表情拉得不省人事了。表情是焦急的笑容。
黄佛成功地将这个故事植入到我的脑海里,因为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故事揭示了他的某种本性。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有鬼,也许还会有鬼。感觉我们正在等待它。
20分钟后,我和黄钊到了单家。一栋两层别墅的地下室里,中间铺着一块白色的短绒地毯。里面堆满了裙子。每个人似乎都能把水挤出来。角落里建了一平米。 1.3米的水泥台面用塑料布包裹,形成淋浴房。床边放着一个单门衣柜,衣柜太高了,大概有两米多高。家具的比例十分不成比例,仿佛是完全不同的人放置在这里的,整个房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荒凉状态。姐妹们,我说,这里太潮湿了,我的骨头缝都起雾了。
单示意我们一起搬衣柜。后面有一扇门,绿色,一米左右高,很窄,没有把手,钥匙孔上贴着一张黄色的笑脸贴纸。
“刚才我躺在床上,听到衣柜后面有‘哒哒哒’的声音,一轻一重,有一种独特的节奏,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一点。”单看着我们,我们也读懂了单的表情。
黄婆立刻做出了判断,说道:“这可是大事啊。”
“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大的?”我问。
我能感觉到,他说。
黄钊撕下贴纸,用一字螺丝刀拧入钥匙孔。传来机械部件未啮合的摩擦声。
“无法转动,里面的锁芯坏了,必须把整个锁盒拿出来。”
单说,你需要得到房东的确认才能找人开门。
如果进不去,那就堵住。黄袍露出了灵感的表情,道:“我们现在就去去找穆罕默德去取鱼吧。”
穆罕默德是我们的大四学生,来自科威特,正在这里攻读商业博士学位。他的真名并不重要。当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的脸时,我们决定称他为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家族从事商业活动,在沙漠国家拥有苏打水生产和供应链。不知道是哪个中国人学会了养鱼的习惯来改善风水的。穆罕默德从唐人街的一家餐馆买了一条金红色的鱼。红龙鱼。老板告诉他,这条鱼可以帮助主人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你明白吗?穆罕默德说得很清楚,并虔诚地称之为幸运。
穆罕默德即将返回中国,到处寻找收养Lucky的人。黄袍伸出双臂,比了比鱼缸的大小,“咱们把鱼搬来挡住门吧。珊,那鱼这么多年了,都当屏风了,只要鱼来了,不管怎样。”就在门的另一边,它不敢进来。”
这是高纬度国家的冬天。下午三点钟天色就开始暗下来,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多了。不管有什么阴谋,都必须做好准备。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浓浓的黑暗向我逼近。车头灯照进来,他们的表情不断变化,不断分散。珊从后视镜里看着我的眼睛,有一瞬间我几乎看到了愧疚。
那天晚上我们收到了红龙鱼,它挂在一个一米长的鱼缸里。水槽顶部的光芒打在鳞片上,红色的纯度就像是从上方某处插入的世界书签。为了我们以后在无法互相指证的情况下,能够轻松找回这一天。穆罕默德身高约1.65米,裹着丝绸睡衣,正聚精会神地与鱼培养感情。水烟从水中溢出,进入穆罕默德体内,然后被穆罕默德吹了半天,又融化进了鱼缸里。他不停地鼓起脸颊,为燃烧的祭坛提供空气,而鱼嘴里居然还真的在轻微地嗡嗡作响。
我想,壁画上疯狂的米开朗基罗画的已经够多了。
我们在Lucky旁边的黑色真皮沙发上坐下。黄婆试图认真地描述单家发生的灵异事件。有节奏的敲击声……衣柜后面的门……黄色的笑脸……他越说,我们就越泄气。
“总之,总之,”黄佛道,“总之,山需要运气。”
穆罕默德重复道,掸族需要幸运。
我们异口同声地看着珊,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后来他们都喝多了,转折点大概是在下雨的时候发生的。我们得到了天气的许可,真诚地成为了暂时的朋友。孤独让我害怕自己会再次成为最后一个被软化的人。
单、黄婆一一讲述故事。单说她记得她的第一个男朋友。他们从初中就在一起了。由于关系的原因,两人考试都没有考得好。对方责备了她,再也没有和她说过话。珊觉得自己错了。从那时起,她就相信别人的命运比自己的命运更重要。正是这些小事,让她的力量越来越弱。正是这些小事,让她的愿望缩小到只是避免心理痛苦。她来到了这里,来到了一个与人生任何一个阶段都不一样的陌生国度,并试图将未来即将实现的生活一一推迟。黄佛再次讲述了他最精彩的故事。跛脚女孩身高只有1.4米。他还是不明白她膝盖的方向。她就像是被什么机器拉了进去,扭来扭去。不幸的是,那台机器是她。母亲的子宫。当时他很饥渴,想勾搭,于是朋友介绍了她。他害怕这座被拆散重组的自由女神像,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和她睡在一起。 “我为什么这么胆怯?”黄婆说,“我不好意思拒绝她,但我对她的热情比我真正喜欢的女孩还要多。”他忘不了她走路的样子,一轻一重,敲着地面那么用力,仿佛在嘲笑他为了虚伪的善良才能做到这一点。
穆罕默德只是坐在那里,享受着在献上鱼之前被感动的感觉。
我们把幸运放在后备箱里。穆罕默德把脸贴在鱼缸上说:“希望幸运能够帮助你。”单拥抱了他,黄袍最后一次拿穆罕默德家族的生意开玩笑。他做了一个给自行车打气的动作,这就是他想象中的向水中注入二氧化碳的动作。 —— “那是一个沙漠国家。他们从事汽水生意!”
我们都笑了,穆罕默德笑得好像有人抓住了某个明显的漏洞,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像穆罕默德这样的人总是会欢迎他的朋友们任意愚蠢的,看来只有成为某种程度的卡通人物才能他与我们无害地混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容忍世界上难以理解的部分的存在。
我们回到路上,方向盘被塞到我手里,由雨滴组成的莫尔斯电码小心翼翼地敲在前玻璃上。当车开到运河边时,轮滑队已经不在了。我们下了车,去自动售货机买了一些。喝饮料,单的手指在荧光玻璃架上摸索着。这时,一名身穿红色流苏拉丁舞裙的女子朝她走了过来。高跟鞋敲击路面的声音在桥下回荡。一层热气笼罩着她的身体,几乎要烧遍这个冬夜。我们都盯着她,我以为我在做梦。
“你怀孕了吗?”黄婆对那个女人喊道,然后我发现她的肚子已经肿得那么高了。
“这是啤酒肚,”女人回答道。
转眼间她就从我们身边经过了。
一回到单家,我们就把衣柜推到墙角,把鱼缸按在门上。山在几步之外困惑地看着它。
鱼缸大约达到门的一半高度,绿色的门有一半从鲜红的鱼缸里渗出来,就像血液顺着一张化学试纸爬上来。
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我问。
珊不再说话。她终于意识到,聚会结束后,她才是收拾残局的人。 Lucky冷漠地挂在鱼缸里。我们都看到它会保护穆罕默德家族的汽水生意,但它却懒得和我们说话。我们只能和珊一起待在这里,直到我们不得不离开。几个小时后,当日光从天花板的地平线上抬起头来,照在每个人湿润的脸上时,我们必然会明白,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但还有时间,所以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谈论着即将到来的假期。单说:“无非是比基尼、伊比沙岛和红眼航班。从她脸上的表情,我知道她已经下定决心要表明她对自己准备面对的事情的无知。”无非是一个陌生人从两张桌子之外伸出的手臂,无非是手掌上画着一张另一个国家的地图。但世界上所有的轮廓都指向一个地方,这就是山一次又一次的承诺。
良久,窗外透出蓝色的光芒,我躺在单家沙发上的编织毯上,头疼欲裂。 “看!”黄袍忽然大喝一声,指着幸运道:“上面有字!”
“什么?”我在Lucky面前扭曲了自己。 “这个词是什么?”
我把眼睛挖进深浅不一的红色鳞片里,却只看到了玻璃罐上的倒影。两个人正在接吻,Huang Pho 和Shan。我没有回头,只是盯着鱼缸一言不发,继续忍受着这无聊的把戏。那一刻愤怒爬上了我的心,那一刻我决定结束我迷茫的青春期。
几乎同时,我们都听到了那个声音。
寂静中,门后传来“哒哒哒哒”的声音,一轻一重,很有节奏,很有格调。听一会就知道这不是误会,这声音充满了用意。黄佛和山同时看向前方,茫然地站着,就像刚刚睡醒一样。我什至没有把目光从玻璃罐上移开。我盯着这些愚蠢的朋友,这些末日里的金色女孩。我并不感到害怕。我以为是孤独让我站在门口。另一边。
“黄婆,”我说,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快要笑了,“也许你的跛脚女孩就在这里。”
//作者:菜菜
//设计:咸味